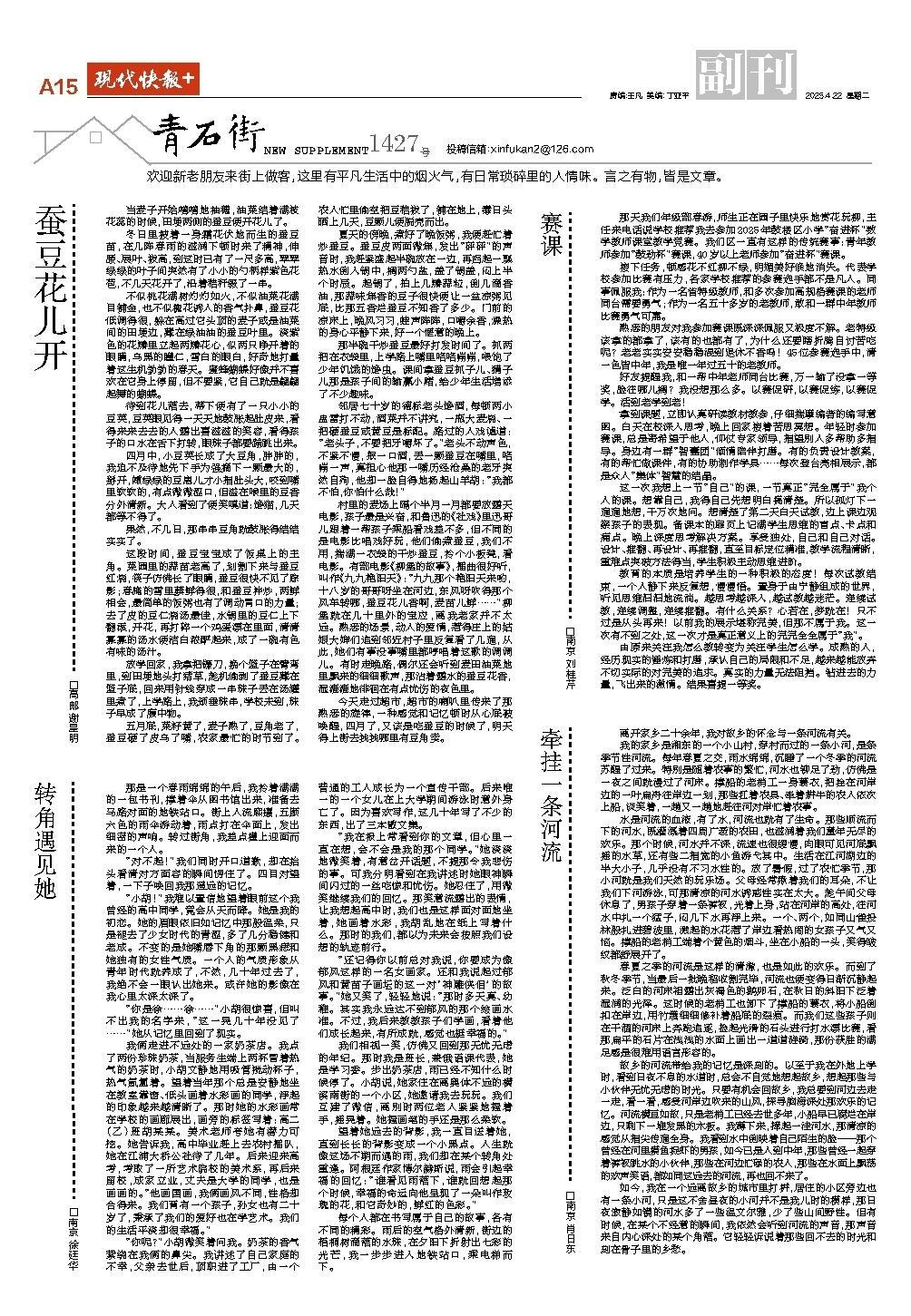□南京 肖日东
离开家乡二十余年,我对故乡的怀念与一条河流有关。
我的家乡是湘东的一个小山村,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,是条季节性河流。每年春夏之交,雨水绵绵,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河流苏醒了过来。特别是随着农事的繁忙,河水也铆足了劲,仿佛是一夜之间就漫过了河床。撑船的老梢工一身蓑衣,把拴在河岸边的一叶扁舟往岸边一划,那些扛着农具、牵着耕牛的农人依次上船,谈笑着,一趟又一趟地赶往河对岸忙着农事。
水是河流的血液,有了水,河流也就有了生命。那些顺流而下的河水,既灌溉着四周广袤的农田,也滋润着我们童年无尽的欢乐。那个时候,河水并不深,流速也很缓慢,肉眼可见河底飘摇的水草,还有些二指宽的小鱼游弋其中。生活在江河湖边的半大小子,几乎没有不习水性的。放了暑假,过了农忙季节,那小河就是我们天然的玩乐场。父母经常揪着我们的耳朵,不让我们下河游泳,可那清凉的河水诱惑性实在太大。趁午间父母休息了,男孩子穿着一条裤衩,光着上身,站在河岸的高处,往河水中扎一个猛子,闷几下水再浮上来。一个、两个,如同山雀投林般扎进碧波里,溅起的水花惹了岸边看热闹的女孩子又气又恼。撑船的老梢工端着个黄色的烟斗,坐在小船的一头,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。
春夏之季的河流是这样的清澈,也是如此的欢乐。而到了秋冬季节,当最后一批晚稻收割完毕,河流也便变得日渐沉静起来。泛白的河床袒露出灰褐色的鹅卵石,在秋日的斜阳下泛着湿润的光泽。这时候的老梢工也卸下了撑船的蓑衣,将小船倒扣在岸边,用竹篾细细修补着船底的裂痕。而我们这些孩子则在干涸的河床上奔跑追逐,捡起光滑的石头进行打水漂比赛,看那扁平的石片在浅浅的水面上画出一道道涟漪,那份获胜的满足感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。
故乡的河流带给我的记忆是深刻的。以至于我在外地上学时,看到日夜不息的水道时,总会不自觉地想起故乡,想起那些与小伙伴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只要有机会回故乡,我总要到河边去走一走,看一看,感受河岸边吹来的山风,探寻脑海深处那欢乐的记忆。河流横亘如故,只是老梢工已经去世多年,小船早已腐烂在岸边,只剩下一堆发黑的木板。我蹲下来,捧起一洼河水,那清凉的感觉从指尖传遍全身。我看到水中倒映着自己陌生的脸——那个曾经在河里摸鱼捉虾的男孩,如今已是人到中年,那些曾经一起穿着裤衩跳水的小伙伴,那些在河边忙碌的农人,那些在水面上飘荡的欢声笑语,都如同这远去的河流,再也回不来了。
如今,我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城市里打拼,居住的小区旁边也有一条小河,只是这不舍昼夜的小河并不是我儿时的模样,那日夜寂静如镜的河水多了一些温文尔雅,少了些山间野性。但有时候,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我依然会听到河流的声音,那声音来自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。它轻轻诉说着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和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